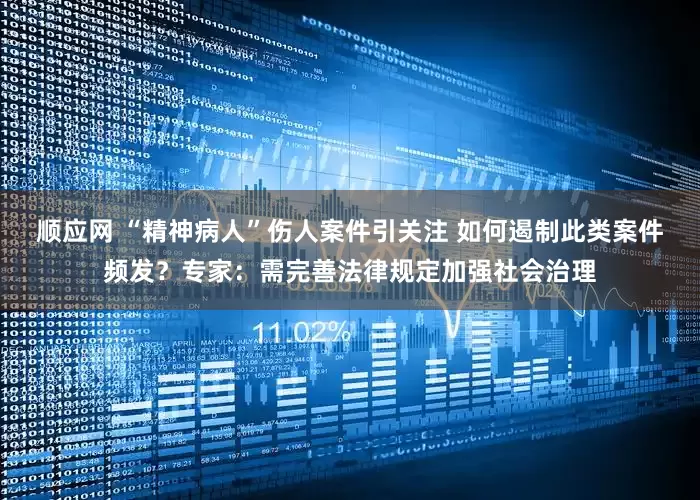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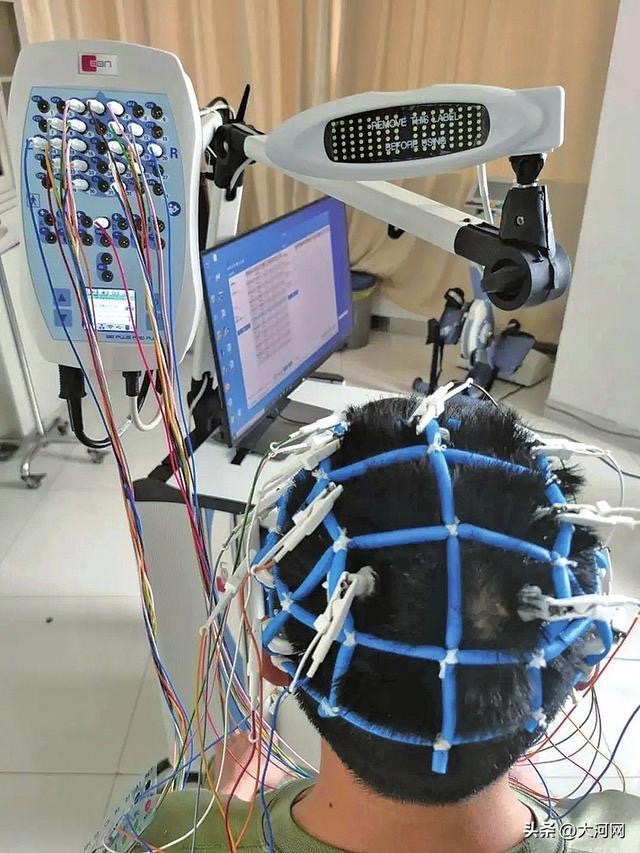
网友热议“精神病人”伤人案件 网络截图
封面新闻记者 邹阿江 赵奕
8月19日,备受关注的“副教授被精神病人杀害案”二审开庭,法院将择期宣判。此案再次将精神障碍患者暴力伤人问题推上舆论风口。
精神障碍患者为何屡次成为暴力事件的实施者?在处理精神病人伤人案件过程中,司法判决面临哪些实际困难与挑战?8月20日,相关专家和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因治疗断档、社会排斥,极易沦为“隐形炸弹”。
此外,律师则指出,尽管《刑法》规定对不负刑责的精神病人应强制医疗,但执行中经费、责任主体不明,制度仍存“落地难”困局,也是未来破解此难题的努力方向。
案件回溯:
副教授被流浪精神病患棍击致死
涉事多方责任认定成案件焦点
2021年11月30日14时许,武汉市武昌区琴园小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51岁副教授王某平因遥控车钥匙声被误认为“鸟鸣”,遭流浪精神病人王某刚持木棍袭击,不治身亡。王某刚经鉴定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发病期,属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2023年8月,武汉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相关新闻截图
刑事判决书显示顺应网,王某刚原在郑州打工,因身体不适返乡。2021年11月29日22时许,其乘火车抵达武昌站后,被民警送至救助站,但因救助站未开门,他在附近吃早餐后流落街头,最终进入琴园小区作案。
据此,王某平家属敖女士认为,小区物业方湖北大学、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及郑州市救助管理站存在救助与监管失职,提起民事诉讼,索赔179万余元,涵盖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
2025年5月,武昌区法院一审判决湖北大学承担全部补充责任,赔偿家属97万余元,湖北大学有权向王某刚追偿;郑州市救助站、武昌分局不承担侵权责任。双方均不服判决并提起上诉。敖女士认为赔偿金额偏低,且应追责救助站与警方。湖北大学则辩称,其已按规定巡逻,王某刚系刻意躲避,物业无法实时防范突发暴力行为,一审认定“承担全部补充责任”属事实错误,超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的“合理限度”安保义务。8月19日9时,该案在武汉市中院二审开庭,11时许庭审结束,法院宣布择期宣判。
对此,8月20日,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良善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本案焦点在于物业是否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审认定湖北大学存在监控失效、未核查外来人员等管理漏洞,构成责任基础。
而难点在于,物业能否预见精神病人袭击?其管理疏漏与命案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救助站与警方是否依法履行临时救助职责,其处置是否存在法定瑕疵,并构成事件的诱发因素,亦是争议关键。”赵良善律师表示。
无独有偶:
精神疾病史伤人案件频发
涉事人员均未纳入有效监管
近年来,精神病人肇事肇祸案件频发。公安部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2年,全国共发生此类案件约1200起,年均死亡超百人。
2025年2月26日,河北廊坊广阳区发生持刀伤人案,致24岁女性周某死亡。犯罪嫌疑人谢某某(33岁)被抓获并刑拘。经鉴定,其患精神分裂症,案发时无刑事责任能力,已被送至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因谢某某作案后有洗澡、换衣、清洗凶器等行为,家属对鉴定结果存疑,已申请重新鉴定。公安机关依法启动重新鉴定程序,案件正在侦办中。
另一起案件发生于2025年3月27日,广东廉江市东涌村叶某持菜刀行凶,致69岁韦某某、36岁叶某花、1岁11个月何某某三人死亡。叶某经鉴定为精神分裂症,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此外,2025年2月26日晚,廊坊一名24岁女幼师被精神病人杀害,凶手谢某某同样被鉴定为案发时无刑事责任能力,已送医监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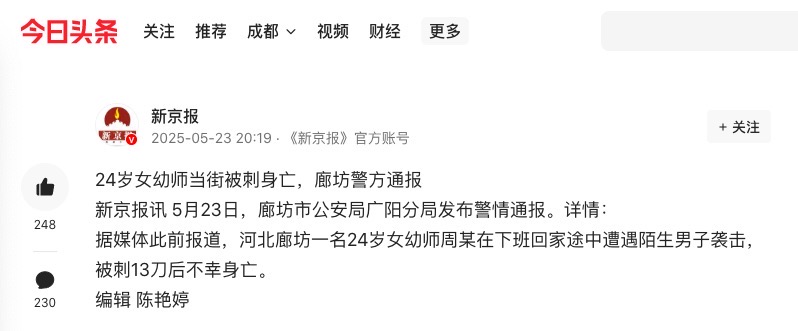
相关新闻截图
多起案件显示,行凶者均有精神疾病史,但未被纳入有效监管,且作案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引发社会对精神病人管理、鉴定机制及公共安全风险的广泛关注。
刨根问底:
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康复资源匮乏
重返社会或成为“隐形炸弹”
追根究底,精神病患者频频伤人,到底是何缘故?有没有相关责任主体对其进行监管吗?
首先是患病人数增加。2019年首次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全国精神障碍患者超1亿人,其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超1600万人,登记在册近700万人,且数量逐年上升。北京某精神病司法鉴定科分析显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涉案中,极端暴力案件占比达94.1%,受害者致死、致残率超50%。
其次,精神科专业人才严重不足。2022年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全国精神科执业注册医生仅5万多人,医患比约为1:2000,远不能满足诊疗需求。
另一方面,与社会治理薄弱密切相关。河北省邯郸市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刘鹏在《法律监督视域下精神病人犯罪治理现状及路径优化》一文中指出,精神病人社会接纳度低,常遭排斥和歧视,而该群体多处于社会底层,因病缺乏生存技能,生存空间被持续压缩。
刘鹏研究发现,近年来精神病患者伤人频发的重要原因是基层服务体系末端缺位。患者出院后常因医保覆盖不足、康复资源匮乏难以融入社会,沦为“隐形炸弹”。他指出,监护责任顺位为:配偶→父母子女→其他近亲属→愿监护的个人或组织(需居/村委会或民政部门同意);无合格监护人时,由民政、居/村委会承担兜底责任。
然而,现实情况是,部分监护人因经济困难、年老体弱或缺乏专业知识,难以有效监管;社区组织和物业公司作为基层力量,普遍缺乏权限、资源与专业能力,无法切实履行照护职责,导致高风险患者处于监管盲区。
治理之策:
精神病伤人担责需分三类情况
加强对其监控并纳入社会治理
精神病患者伤人就是“免死金牌”?随着多起“精神病人”伤人案引发关注,有网友担忧,精神病人犯罪通常不承担刑事责任。
对此,8月20日下午,北京华让律师事务所薛媛律师向记者表示,这是公众对法律的误解。她解释道,根据《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控制行为时造成危害,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犯罪,应负刑责;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者,应负刑责,但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当前,我国针对精神病患者暴力防控的法律法规已经有所完善。《精神卫生法》实施后规范了诊疗与社区管理,《刑法》《民法典》明确了强制医疗条件与监护人民事责任,部分地区也出台了细化管控政策。
不过薛媛律师指出,当前仍存在一些管理缺口,例如精神疾病患者数量持续增加,鉴定标准与程序需持续优化;精神鉴定由公安机关单方启动,缺乏复核与监督机制,影响公正性;社区监管流于形式,协助管理职责不明确,履职不到位无追责机制,且现有措施能否有效预防暴力行为仍存疑问,亟待系统性完善。
那么,除了案发后刑事责任认定,如何从源头破解精神病人犯罪这一社会治安顽疾,减少案件发生?
实际上,近年来不少法律界人士就此建言献策。其中,2017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郑尚伦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精神障碍患者信息库,实现民政、公安等部门信息共享;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提出,应将精神病人管理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由卫生、公安等部门各司其职,建立以社区为依托的网络监控体系,及早发现发病征兆,督促监护人落实约束与治疗。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谢澍在接受采访时提出建议,一方面需完善法律规定,明确强制医疗程序的解除标准;另一方面应加强社会治理,建立精神病患者风险评估数据库,对高风险群体实施动态监控。
他指出,多起案件暴露出精神障碍患者管理中的治理断裂,核心在于如何平衡患者尊严与公共安全。法律完善、监护责任明确、社区康复体系建设及多部门协同机制等问题,还需要未来不断厘清与优化。此外,精神病患者家属同样应该承担起责任,做好监护人职责,多关心,多陪伴,及时制止可能的事故,减少犯罪案件的发生。
【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封面新闻】所有,今日头条已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顺应网,任何第三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迎尚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